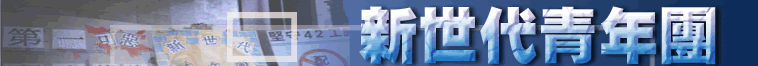本文刊登於:「新世代青年團」(http://youth.ngo.org.tw/)2005.05.11
「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與商品拜物教
文/KILASME
接觸了娃達(AGNES
VARDA)的「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拾穗者們與女拾穗者)這部紀錄片後,有種相見恨晚的感覺,來不及逐一研究她每一部作品,尤其是關於她其他紀錄片,但單就這部片子本身的文本而言,其中對於撿拾(拾穗)的行為,提供我一些申論的元素提出我對當今商品社會的反思,而同時也就被撿拾的對象:垃圾(取其廣泛的定義)裡去揀取關於此部片記錄行為本身和挖掘垃圾的同質性。
雖然AGNES VARDA(愛格妮絲.娃達)自己常言:「記錄片最好的朋友叫做運氣!」但我則認為所有“記錄”或是“撿拾”本身皆是有跡可循。
影片簡介
以下,只是一段網路上關於AGNES VARDA(愛格妮絲.娃達)與她的紀錄片「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拾穗者們與女拾穗者)的介紹:
「一部以DV拍攝的低成本實驗性藝術紀錄片,在兩年多時間裡參加了幾乎所有的重要國際電影節,並且獲得三十個獎,無論如何不能不算是奇蹟,導演就是享有〝法國新浪潮之母〞美譽的愛格妮絲.娃達。本片於十二月十三日在洛杉磯獲得第三十個獎,即國際紀錄片協會頒贈的“先鋒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至隔年四月,年過七旬的娃達帶著數碼攝影機,在法國鄉村“閒逛”的過程中,親自拍攝了一些關於當今拾荒者的影像。娃達將形形色色的拾荒者分為三類:有些人拾荒是因為生活所迫,有些人拾荒是因為他們是藝術家,有些人拾荒因為他們喜歡拾荒。摘自http://www.filmsea.com.cn/zhuanjia/article/200309190011.htm」
拾穗的計量單位與拜物教的展開
片子一開始即用法文字Glaneurs的第一個字母“G”作為開頭,用文字定義拾穗者逐漸展開成用影像定義拾穗者,這似乎暗示了人類文明的展開,由文字開始,文字成為一個細胞,接著構成片中大量出現的導演的旁白,語言成為一種書寫一種表達的細胞,而跟著影片逐一暴露的大量的被丟棄或被撿拾的萬物撿影“商品”,商品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佔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娃達作為一個拾穗者本身她所撿拾的範疇,無一倖免的皆成為物與物交換關係之下的臉孔。
娃達非常明快的先用一位老女人受訪者開始喃喃她母親是如何教導她拾穗的美德,這美德的箴言從母親這樣一個角色說出便清楚表達母體生產萬物的基本原則,然而這美德並未延續多久,不一會的功夫即成為美術館裡供人朝拜的藝術品,歷史上拾穗的女人們的美德被錶上了框,她的提醒功用被動的不再,她成了一項有價的物,來往的人群只為拍照留念,參觀美術館成了現代文明人一項重要的消費。當來往的參觀人潮駐足拾穗畫前,他們的臉彷彿能感受到這些畫帶來一些美的經驗甚至有什麼神性體現在上頭,然而鏡頭一轉衝入不協調的街頭rap,rap歌詞講著一群可憐的拾荒者並搭配清道夫清掃街頭的畫面,此時,神性流落街頭了,成了眾人趨之唯恐不及的垃圾。
影片隨著一車車的馬鈴薯傾倒,商品構成的世界逐漸赤裸地呈現在人們面前,無論他們是發芽的有機物全都成了無機的商品符號。拾穗不那麼形而上了,她逐一成為資本家監督之下可以計量的行為,就像馬鈴薯必須長成2~4英吋,5.5磅可以賣11鎊、人們撿那些超出規格的,而撿拾被棄馬鈴薯且賴以維生的失業貨車工人就曾是開著每天娃達在公路上喜愛看的貨車,一部一部的貨車載著賣出與賣剩的商品,這名失業司機未失業前,一天工作21個小時,司機的勞動力成了可以計量的數字、一個特殊的商品,而他的命運就像那些不符規格的馬鈴薯被隨意棄置。拾穗的計量逐一展開,除了葡萄園的商業利益限制採摘外,蘋果園老闆為節省清理費用,只要民眾註冊就可以帶走100磅的蘋果或是更多剩下,然而無論如何採摘,依舊會剩下10噸,民眾成了免錢的又可以挑剔清潔工,他們撿拾好的丟棄壞的,因為生產過剩。或海邊的居民擁有一本潮汐手冊,牡蠣業者允許居民在聖誕期間的大退潮時撿拾牡蠣柱外10碼的散落牡蠣或蛤,11磅的牡蠣與7磅蛤,彷彿大海天生就是資本家的,而資本家插了幾根柱子在大海裡,牡蠣從長殼那一刻天生就是商品一樣。的雖然娃達像戀物般用了兩次手中的DV近攝與放大馬鈴薯及紫色甘藍菜的特寫,試圖提醒觀眾物的原始樣貌,資本主義無機的交換關係下有機的存在,物他原有的使用價值,特別她鍾愛呈現可吃的食物:生存的能量來源。然而拜物的神秘繼續體現在她所撿拾的人們上頭。
接著娃達呈現一群年輕人破壞超市的垃圾桶的官司,超市經理氣急敗壞指控年輕人們蓄意破壞其私人財產,可年輕人卻說他們只是拿了垃圾桶裡不要的過期罐頭,娃達用一名身穿律師袍的女律師說著年輕人的違法亂紀,而之後她又用了另一名身穿律師袍的女律師用它社會賦予的權利站在被丟棄的家電產品堆中宣讀:「物品一但被拋棄就是沒有主人了,人們可以隨意拿走他。這是完全合法的。」就像片子那個在採收後的甘藍菜園的男律師也朗讀著古法典:「採收期後允許可憐的人們進入撿拾……」這三位擁有社會公認的行使公權力角色在娃達鏡頭裡成了可以互相嘲諷的角色,然推到原點,商品天生成為了法律控管之下的守法公民,只是他沒有投票權罷了,一但商品被合法的拋棄了,這位公民的唯一義務便是成為私有財產。
馬克思對於商品的拜物教性質有段生動的描述:「起初人類製造一張桌子,可是桌子還是木頭,還是一個普通的可以感覺的物。但是桌子一但變成商品出現就變成一個可感覺又超感覺的物,他用腳站在地上,他的木腦袋裡生出比他自動跳舞還奇怪得多的狂想……。」片中一名三星級的大廚,用其老祖母的訓誡說出撿拾的美德,他撿拾著地上掉落的蘋果然後用其烹飪,某種程度上而言,他撿起了不要的垃圾然後烹飪,而他的菜單標價100元美金,這“100元美金”使人們產生幻覺。而吃這些蘋果做成的菜的人往往厭惡垃圾甚至同情那些撿拾的行為。因此人們的感官需藉由貨幣形式的認可,他們的感覺在貨幣之下變成了超感覺,所有的興奮乃自高潮都在“合法”的情況下產生。諸多計量的單位所掩蓋的正是一種如馬克思所探討的「貨幣形式」,在商品的價值形式不斷的過渡之下,「貨幣形式」被確定下來,10噸馬鈴薯、100磅蘋果、10磅牡蠣…皆共同有著相同的等價物,那便是某個單位的貨幣,這是當今人類共同的命運,我們只要無法取得貨幣,那麼遲早有餓死的一天。商品拜物教的迷就是貨幣拜物教的迷。
片中另一名活蹦亂跳的被紀錄者,擁有固定工作和收入並享有社會福利保障,但是他卻吃了十五年的垃圾,他的飲食百分之百靠垃圾桶裡的丟棄食物,這位自嘲為他人眼中激進分子,說了一則至理名言:「人們依賴使用期限過活,用鼻子聞就知道東西壞還是沒壞。」的確,人們對存在的背書由貨幣又多了一項“使用期限”,可當他忿慨指責過度的消費破壞其他生物生存的權利,畫面呈現商船的漏油害死了無數他鍾愛的鳥類時、娃達接著拍攝他腳上的膠鞋,膠鞋也是石油提煉物製成的商品,娃達問他穿膠鞋的原因,他則說他愛死了穿膠鞋,讓他就像行走在這都市像是土地的領主,可這段影像,即便讓他像極了飛凌於都市垃圾之上的鳥兒,然而這都市的鳥人也是啃食著都市生產過剩的產品過日,他的雙腳上的膠鞋看不到任何人類勞動的價值體現在上頭,膠鞋只是一雙膠鞋,一個可以交換的物,遺世獨立的他就像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被埋葬在物與物的關係的虛幻形式之下。
影片到了中間,娃達終於大剌剌地走入私人的無花果園開始進行採摘行為並大快朵頤一番,但在之前,娃達下了幾則有趣的注解。她先放入了第一對葡萄莊園的老夫妻,莊園主人老先生本身覺得撿拾的行為很可愛,可是法律規定葡萄園不能撿拾,他同時又兼具釀酒師和臨床心理學師兩種身份,但是老先生所研究的哲學命題叫做「反自我」,因為老先生覺得他過著兩種身份,但這兩種身份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其實代表的是相同的階級,就是「中產階級」,娃達不提供批判,她只加入了這位研究“反自我”的中產階級老先生留做伏筆,再來的第二對夫妻也是對中產階級的夫妻,其中太太很用力的解釋她喜愛的撿拾行為是種充滿雅趣的行為,她撿拾那些不發芽的東西,並談到她如何愛上她丈夫,她第一次看到她丈夫,是頭戴紅色的貝蕾帽、身穿芥茉黃的褲子,腰繫一條彩虹的腰帶,她承認很難不被其吸引,而她丈夫則說對她一點印象都沒有,這是娃達有趣的安排,中產階級仰賴自認的品味與主流符號,他們甚至是過度消費的族群。而在這兩對夫妻之後,娃達入鏡,摘起樹上的無花果吃,而邊吃邊丟像個不受控管的小女孩,娃達本身反映了她在社會的符號象徵:法國新浪潮教母、當代重要女導演、某製片公司的投資者……她帶著她的社會地位然後像她所紀錄的邊緣拾荒者一般吃著,而且陶醉著,然後邊詢問身旁的園丁是否允許採摘,答案是否定的。娃達繼續啃食著多汁的無花果,就像失樂園裡的夏娃偷嚐禁果,似乎一邊挑戰資本主義社會既得利益者的神權也一邊打破觀者的期待,拾穗者的多重身份:也許帶有中產階級的品味、或許是基於自我或反自我、是種反省的行為、被邊緣化不得不的選擇…,似乎都因為她入鏡的撿拾與採摘行為得到了統一的幻象,觀者無法在她身上尋求某一種固定觀點,她同時拒絕了主流社會對於那些被邊緣化的拾荒者的凝視(註1),也開始了自我的凝視甚至是主動爭取凝視,藉由自己的不斷入鏡來達到自我的對話與邀請觀者聽她說話,她所透過鏡頭撿拾的一切是她想說的。
然拜物之外呢?她用一位擁有碩士學位卻住在避難所並無償地教導避難所的文盲們讀書認字的拾荒者作為她所撿拾的拾穗者們模型的典範,娃達在二○○四年台灣台北舉辦的「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座談會上,她特地剪了這位都市隱者的紀錄畫面當作對「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這部紀錄片的介紹,她並重複了好多次自己對他的欽佩,而或許在這顛倒的只有物與物的關係的資本主義世界,像片尾這號人物,拾穗無法在他身上計量、拜物無法在他身上開展,娃達或許不說教,但她允許自己在這樣一部紀錄片留有一記安那其式的書寫。
而拾穗者們撿拾的究竟是怎樣的東西,不論是樹上掉下的落葉、果子或卡車上丟下的蔬果、或廢棄的各種生活用品,在娃達的定義皆是:垃圾,這些垃圾們是沒有主人的物。而娃達繼續帶著她手中的DV(這個在未來可能變成垃圾的工具)繼續撿拾關於垃圾的資訊。那些由碳水化合物構成的可食的垃圾變成了拾穗者們的生命延續的能源,而那些由各式化學元素構成的不可食的垃圾則成了拾穗者們生活用品或是創作的材料。
娃達連續訪問了三個〝藝術家〞,他們皆是用垃圾來創作,第一位是個業餘藝術家是個小夥子,他將成堆的垃圾撿回家建築了他的小洞窟,他喜歡他的垃圾洞窟,垃圾本身的結構斷除社會脈絡,其交纏的就像宇宙的蟲洞(註2),垃圾是沒有階級的,他們共同的命運是被逐出與拋棄,垃圾是沒有交換價值的,他們身上的顏色或是標籤僅僅只是一層外皮罷了,垃圾交疊在一起,是終點也是起點,垃圾築成的洞窟是沒有時間的。
而對於垃圾的記錄是否也暗喻此部紀錄片記錄行為的本身,娃達撿拾的或許是在這充斥著垃圾資訊的年代裡她認為有意義的資訊,這些拾穗著變成了一則則資訊,只不過他們可能是被主流排擠下的資訊,娃達甚至就明白認為撿拾就是一門藝術,如她採訪的第二位受主流肯定的藝術家Loui’s Pon,這位也用垃圾創作的藝術家,其作品被印成精美的刊物,他帶著詩意的口吻說著:「我就像在翻字典一樣,每一個垃圾都有他的故事,我用垃圾來造句,藝術只是整理的工作,我使他們重生。」如娃達的撿拾行為同時就是一種記錄行為,觀者也可以如那些拾穗者們依其需要隨意擷取片段資訊(垃圾)或任意前進與倒退,甚至拼湊某些觀點(就像我現在做的事一樣),一個紀錄片作者試圖凍結時間,將之捕抓下來,如她撿拾回家的一只沒有時針的鐘,記錄者是一個最大的拾穗者,紀錄片和垃圾堆的道理在這裡就顯得很類似,而本片企圖捕捉某種人類生活,然而在人類生活分為精神和物質世界下,這兩者罕有完全吻合,若無衝突也充滿緊張關係,而許多紀錄片往往只傾向一點,且以精神層面居多,此片精彩之處在於展現人的精神和物質世界居然緊緊相扣,就像前面所言,彷彿人類天生下來就是個商品,或彷彿只要拿起DV,每個人都可以是紀錄片工作者一樣,就像在垃圾堆中,垃圾的相關研究裡,你以為只有物質的分析,然而卻從中可以歸納太多人類因精神層面所遺留下來的證據,在《垃圾之歌》這本書裡,作者將垃圾堆比為萬年鎖鏈,書裡談到:「人類一向留下許多描述他們生活和文明的記載,但那些記載很多不過只是自我吹噓的廣告。那些社會菁英份子的墳墓、廟宇和宮殿遺跡中,處處可見崇拜他們的親人和諂媚家臣所記載的個人事蹟……我們可以理解歷史學家必然會為這些證據所吸引,但是垃圾卻像是茶餘飯後的閒談,反而更能忠實明白的記錄事實」。這同時也體現在最後一位藝術家受訪者上,是位很老的老先生,喜歡撿拾殘缺的洋娃娃鑲嵌在他的房子,他妻子肯定他的行為像位藝術家。當老先生同娃達說非常喜愛洋娃娃後,隨即開心的牽起身旁同樣老朽不堪的妻子的手,可以感覺那妻子的手就快要粉碎而死去,然而對照其身後的垃圾碉堡,可以想見百年之後,這些由塑膠製成的垃圾依舊存在,就像娃達自拍自己老朽的雙手對應於永遠不會老去的林布蘭肖像畫,這裡又讓我們洞見一件事情,是否藝術品之所以為藝術品乃是他比人類晚一點死去,那麼垃圾果真為藝術品之首,若說藝術品存在提醒著人類文明的某些啟示,那麼垃圾可能陪伴人類文明長長久久,終其一生都在提醒著某些啟示。
而拾穗的行為(拍攝紀錄片的行為)也非研究數學公式般,就像人類世界之於垃圾堆一般也非一張只有年表和分類的紙張,但娃達放了小朋友們在學習及玩弄那些大人們清洗乾淨,顏色漂亮的垃圾,並試著將之回收利用…「可小朋友敢跟清潔隊員握手嗎?」這是娃達唯一提出的問題。這也重疊了紀錄片工作者的大栽問,撇開諸多的拾穗者群象,單就紀錄片工作者本身,即便DV的產生帶來了笨重繁複影像拍攝工具的革新,似乎也打破了某些體制的壟斷,但也並非全然的自由,只是又順應新的體制,紀錄片是觀點的再現是去建構出來的事實,即便突破了什麼,但又產生新的問題,而唯一從拾穗這擋事上頭只能直覺的公約成:現象只有一個,但其構成因素卻不相同。藝術是見仁見智的、垃圾是見仁見智的、拾穗是見仁見智的,觀看紀錄片本身也是見仁見智,但其存在卻能有效提醒人類一點:「許多我們自以為了解的事物,事實上我們不見得知道。」所以娃達在片尾除了丟出一個無政府主義的現代隱者外,也將最後一個鏡頭留給她終愛的繪畫《一群在暴風雨中拾穗的女人》,或許在畫家作畫的同時跟她在拍攝(拾穗)的同時是一樣的,那是一種神性的交流,畫同時也在當下的時空於大風中擺盪著,她藉由鏡頭的凝視達到和畫作的神交,回歸到個人最直接的時代見證,如同那位畫家和她自己,誰也沒辦法有答案,那答案恐在觀者將影片重新播放時,才能洞察到沒有開頭也沒有結束的洞察。
(註1)《無法無家》裡的凝視:以獨特的攝影機運動產生某種疏離效果,最終以干擾或阻隔帶有性欲成份凝視的場面調度方式來達成父權凝視的「散佚」(Flitterman-Lewis / 1990:307)。易言之,女性主義電影理論認為,電影意義的生成與藉由凝視以建構女性作為影像意淫客體的方式緊密相連, Varda 據此挑戰主流編碼,以凝視的再引導,或 Flitterman-Lewis 所謂的父權凝視的「散佚」(“dispersion”)加以挑戰,藉由賦予片中不同見證者人物的觀視點(Mona 作為容易捕獲的性獵物、 Mona 作為自由無拘的象徵、 Mona 作為令人好奇或鄙視的女人),使觀者不必然認同男性的觀視或女性的觀視,因而可以在游離與分裂的版塊上任由觀眾重組 Mona 的不可能的肖像。在此辯證觀點下,導演拒絕主流敘事電影剪接慣例下具有專斷性的特定凝視方式,因此提供了觀眾認同的可轉換性,在帶有疏離效果的自主性省思下,觀眾參與了社會性別議題的影片言談建構過程。摘自吳珮慈教授改寫自其個於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發表於中央研究院「婦女史與性別研究學術座談會」之「電影與性別研究」引言稿──《女性主義電影論述與實踐每兼論艾格尼絲.娃達的電影書寫》。
(註 2)蟲洞:一種連接兩處時空的特疏通道,讓人類可以瞬間穿梭宇宙是做時光旅行。
參考書目及資料:
馬克思《資本論》卷一 人民出版社 ISBN 7-01-000172-3/A.66 2001年第12刷
威廉.拉瑟基(William Rathje)與古倫.墨菲(Cullen Murphy)《垃圾之歌》(RUBBISH ~ The Archaeology of Garbage)時報出版社NEXT系列13 ISBN 975-13-1118-9
吳珮慈「永恆的影像拾穗者∼艾格尼絲.娃達」
單萬里「阿涅絲.瓦爾達∼新浪潮教母的今天昨天」2003-09-19
http://www.filmsea.com.cn/zhuanjia/article/200309190011.htm
洪國均「造反策略∼從紀錄片反寫實的可能性談起」Fa電影欣賞季刊第111期
陳儒修「紀錄片:「記」什麼?「錄」什麼?又是什麼「片」?」Fa電影欣賞季刊第111期
郭力盺「這是我的影像,這不是真的」Fa電影欣賞季刊第114期
媒體與文化(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大眾文化研究專站)
http://www3.nccu.edu.tw/~yfko/page3-2004-2.htm
歐貞延「網路自拍文化∼從暴露狂到自拍」
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334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