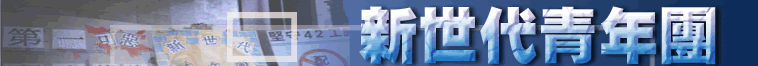【讀者投稿】
本文刊登於:「新世代青年團」(http://youth.ngo.org.tw/)
2004.01.30
貢寮核四廠週遭環境參訪記
修倫
二○○四年一月一日,在一個略顯陰鬱但仍然十分舒爽的早上,我們幾個《台灣環保問題面面觀》的課堂伙伴,在輕車簡裝下,經過了深坑、石碇、平溪、雙溪,沿著台106線道與102線道,穿過北台灣美麗的山野,來到了位在澳底貢寮鄉的核四廠。徐文路老師在車子行經過福隆火車站,左拐右轉了幾個彎後,指著路旁的幾幢看起來還十分堅固的鐵皮屋,告訴我們,那是鹽寮反核自救會包圍核四廠的陣地,現在大概也已經廢棄了。車子很快地停到仁和宮前的廣場上,另一部車子上幾位熱心長期從事環保運動的朋友,已經在等候我們。他們領著我們這幾個長久居住在水泥叢林,在政府長期的政令宣導和媒體與社會過於泛政治化的氛圍,而對於反核運動一直抱著敬而遠之或是同情但疏離的都市人,一步一步登上仁和宮的屋頂,第一次正視居住在鹽寮與貢寮地區居民超過十五個寒暑的夢魘。
◎仁和宮
仁和宮,供奉著討海人心中的女神媽祖,是一棟十分現代化的建築。在水泥與瓷磚所砌起來的二層樓建築中,有幾處彩繪雕刻著傳統飛簷和裊裊不絕的焚香氣味,讓人意識到它的宗教意味。從仁和宮的屋頂往核四廠的建地望過去,會訝異地發現核四廠其實很近,大概只有數十公尺之遙;仁和宮臨馬路的另一邊,即是澳底的鹽寮/貢寮社區居民生活的聚落,海產店與各式商店沿著馬路密集地開著。向南往三貂角的方向望過去,可以看到發電機組的預定地;沿著海岸往北看,可以看到為了運送發電機組與未來的原料與/或廢料所建的重件碼頭。為我們解說的先生在和風徐徐地吹動中,告訴我們這片廣袤的核四建地的大致地形與建設規劃。我靜靜地聽著他的解說。聽他告訴我,哪兒是當初日本人在馬關條約簽定後,登陸北台灣的地方;哪兒又是凱達格蘭族海上長城的遺址,那個可能比起八里鄉距今二千三百年前,但因為污水處理工程而幾經破壞殆盡的十三行遺址更古老也更龐大的文明遺產,因為劃歸為核四的建地中,可能也已經步上十三行遺址的後塵,永遠消失不再。我想望著,一八九五年五月底,日本新任台灣總督兼軍務司令官的海軍大將樺山資紀所派遣的近衛師團,在澳底(一說在更往南二公里處的龍門海灘)登陸,展開其後五個月左右的收服台灣的歷程。這個地方,是台灣史上應該被記得的地方,在過去,被日本人立了個登陸紀念碑,國民黨接收台灣後,改為抗日紀念碑,現在則是經過數百萬公帑重建的鹽寮公園,卻已經因為核四廠機組運轉所設計的海水降溫出入水口工程,而廢棄在馬路旁。
◎等待果陀
接著,我們往福隆海邊過去,去看看因為重件碼頭的建造,使得在短短三年左右的時間,原來名聞遐爾的雙溪河與福隆的沙嘴,已經成為旅遊手冊上供人憑弔的記憶。我們來到阿英姊的店,一個販賣各種海邊戲水物資的店。紅的、黃的、碧藍的各色泳裝,高掛在店門口,一旁還有捉魚用的各式小魚網、魚鉤以及戲水用的浮板,在冬日的陽光中,不禁露出一股蕭瑟的氣息。阿英姊和她先生熱誠地的招待我們這幾個陌生的都市人。
前環保聯盟台北分會副會長簡淑慧小姐告訴我們,阿英姊曾是鹽寮反核自救會的副會長。簡小姐曾在課堂上說過,在鹽寮/貢寮這一帶,因為長期的反核運動,使得此處上至六、七十歲的老人,下至五、六歲的小朋友,都可以說出深刻而條理明確的反核理由。然而今天,阿英姊顯得無力而沉默。向陌生人敘說核能電廠正反利弊的熱誠,已被長久政治上不負責任的承諾,一點一滴的消磨。在長達十多年的抗爭、失敗、再抗爭、再失敗…的過程中,老成凋零,後繼乏力。當我問起今日自救會還有多少人時,阿英姊嘲弄地說,還剩下她一個人。我繼續嘗試地詢問她未來將如何繼續反核時,她淡淡的說,她在等待「真」。看到我們似懂非懂的眼光,她稍微解釋了一下:「現在社會到處充滿了假」,「我現在就只能看著」,「等待真的出現」。這如同謁語般的話,為我的問題劃上句號。她客氣地請教我們這幾個外地人有什麼看法,我們間歇地的談到進行政治體制內的努力與體制外的抗爭,但我知道,這些無論是訴諸於政治操作──利益團體的遊說與立法院前的遊行示威,還是暴力的抗爭──以身體衝撞、包圍核四廠,她/他們都曾,甚至將繼續嘗試。當我們課堂上的一位伙伴建議她不要放棄政治的道路時,她語帶無奈的說,當初反對核四的一些人,無論是已經是具有政經實力的政治人物,還是因此而當選地區或中央的民意代表,最後都背棄了他/她們當初的承諾。「連總統都給我們當到了,又怎樣?」
◎百日歡顏!?
二○○○年三月十一日總統大選前夕,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先生簽署了鹽寮反核自救會所提出「停止興建核四廠」的承諾書。七天後,陳水扁當選了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結束了國民黨五十多年一黨專政的歷史,取得執政權,也讓長久和民進黨反對運動友好結盟的許許多多社會運動團體大為振奮,這其中,當然也包括貢寮地區反核的居民。然而,政權轉移後,朝野的爭鬥,正式以社會正義放兩邊,政治鬥爭擺中間的姿態展開。核四的建與廢,無疑地成為政治鬥爭最佳的角力場。在歷經二、三個月的政黨惡鬥後,各黨派終於有開始尋求和解/和平共存的意識,於是「扁郝會」、「扁宋會」、「扁連會」,在一個行政院長的來去之間,接連展開。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就在朝野好不容易裝扮出來的和解大戲要畫上句點之時,陳水扁政府的第二任內閣首長張俊雄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姿,發佈了核四停建的重大決策,將整齣和解大戲一筆抹消,開啟了也許是台灣島上自一九七九年中美斷交以來最為晦暗動盪不安的一百一十天。但,諷刺的是,卻同時可能是貢寮地區反核自救會居民最為高興的一百一十天。阿英姐的丈夫,在我們進來後,一直默默而友善地張羅著茶水、水果與點心,在我提問他們如何看待該次停建核四的宣告時,他納納著說:「辛苦奮鬥十多年,高興一百多天。唉!這一百天,他們還來…。」我狐疑地問:「他們來幹嗎?他們是誰?來威脅、恐嚇你們嗎?」阿瑛姐的丈夫,嘆嘆氣,搖搖頭,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二○○一年二月十四日,同樣由行政院長張俊雄先生宣布:「核四即日起復工。」夜未央,夢魘繼續。
◎浪淘盡,福隆沙灘
在我仍在嘗試釐清腦中關於核四的種種訊息時,大家決定去海灘瞧瞧。我們漫步到冬日寂寥的福隆沙灘。由於久聞其大名,我帶著空白的期待來到沙灘。當我正狐疑地看著底下滿是沙地上長長的跨海大橋時,喜好旅遊同時因為工作關係而完整跑遍整個東北角的課堂伙伴,憤憤不平地告訴我,這些沙,是去年暑假福隆音樂祭時從別處運來的。徐老師也說,聽說花了五百多萬的經費才造出這一片沙灘。跨海大橋的盡頭,就是海。沿著海岸往南看,是台灣的東北極點──三貂角;往北看,是核四的重件碼頭。徐老師解釋說,因為重件碼頭興造了南堤與北堤,阻礙了海水的迴流,過去名聞遐爾的沙嘴,如今已消失了;同時,也造成重件碼頭的淤積。面對這樣一幅詭異的景色:跨海大橋如今跨的是沙,橋的盡頭是海。真是令人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
當我們結束短暫的沙灘漫步後再度回到阿英姐的店時,阿英姐招待我們吃著名的福隆便當與新鮮的魚湯。在填飽肚皮後,由於對於福隆的過去完全沒有印象,我向阿英姐提問關於我在海邊所看到的那幅「異景」。阿英姐忽然激動起來,她翻出福隆美麗的過去,以及沙灘大量消失、繼而消失殆盡的照片。我看著那曾經存在的雙溪河,跨海大橋下,有人在戲水、衝浪;橋的盡頭,是長長的沙嘴,人們可以漫步過橋,走到隔絕雙溪河與大海的沙灘上。這橋,曾經本本份份地擔任過跨越水面的職責,如今,卻因為核四的建造,詭異地通向大海,而非陸地。阿英姐忽然抖擻她的精神,開始為我們解釋起沙灘消失的原因。
澳底,地如其名,位於台灣東北部三貂角與鼻頭角兩個岬角之間,承接著來自北方沖繩海域黑潮的沖刷,海水從三貂角沿著海岸往北沖撞,最遠可到鼻頭角,在天然地形的作用之下,自然地迴流,海水因此將沙子再度沿著海岸線往南帶,又帶回福隆一帶堆積。如此週而復始,造就了福隆厚實而細密的沙灘。然而,重件碼頭的興建,截斷了海水的自然迴流,於是,海沙有去無回地,或沉落到海底,或淤積在重件碼頭,雙溪河因而得以沖過日益稀薄的沙嘴,改變了福隆海灘原來的景觀。河水與海水的直接接觸,進一步有可能造成河水與沿岸土質的鹽化;而沙灘的流失,不但海岸面臨了海水的直接沖擊,也宣告當地觀光產業的冬日將無止無休。即便雇人工、花鉅資堆積出來了一片沙灘,也是枉然。阿英姐嘲弄地說:「因為少了沙嘴,使得戲水不再安全。福隆音樂祭,雖然吸引來許多人潮,但因安全起見,禁止遊客戲水。」
◎媽祖無言
我望著這些曾經自然存在的美景,這些對於澳底貢寮居民,曾經那麼理所當然的存在。百千年來去而復返的海沙,因為人的力量,在短短三、五年內,消失殆盡。在經過幾番短暫的討論後,我們決定再沿著公路看看海,阿英姐十分熱誠地送我們離開。離開前,我又瞥見那些孤零零、艷麗高掛的泳裝,更襯著阿英姐,以及許許多多貢寮人和反核運動者的無奈與蕭索。這個純樸的北台灣濱海的小鄉鎮,因為一九七八年台電籌建核能四廠會勘建議貢寮為最優選擇,與兩年後原委會通過貢寮為核四預定地後,捲入了往後台灣歷時最長久、涵蓋層面最廣的社會運動。一九八八年鹽寮反核自救會的成立,開啟了貢寮鄉居長期而又艱苦的與政府溝通與抗爭的歷史。這個歷史,還會繼續下去。雖然自救會與當地的居民,在和政府的對抗過程中,早已傷痕累累。政治人物的欺騙、訛詐、拖延…使得反核、反核四,成為政治鬥爭的資本與籌碼。問題的焦點早已在政治口水中模糊。自然的、人文的與社會良心,在幾番核四建/廢攻防戰中,消磨殆盡。但她/他們仍然選擇繼續反對,等待社會「真」的出現。
望向海天的盡頭,幾艘出海捕魚的漁船依稀可見。太平洋沉默著,海水或起或落的刻劃台灣的邊線。仁和宮的神龕上,媽祖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