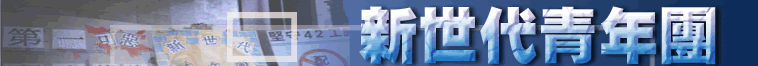讀者投稿
本文刊登於:「新世代青年團」(http://youth.ngo.org.tw/)2004.04.30
我們為什麼要組織教師工會?
羅德水(台北市教師會總幹事
)
經過數月籌備,「全國教師工會」已經於九十二年十二月六日在台北成立,台灣長期以來沒有教師工會的難堪處境也終於得以改觀。
即便如此,一直到今天為止,仍然有人要問,我們為什麼要組織教師工會?作為一個實際參與籌組教師工會的基層教師,筆者願意就以下諸多問題就教各方先進。
首先,我們最被常問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教師是勞工嗎?」而毫無意外地,也有不少老師嚴厲地批評我們,為何寧願放棄教師的「尊榮」去當一個工人?
關於這樣的指責,我只想反問,教師不是勞工,難不成會是雇主嗎?無論教職多麼清高神聖,也全然無法改變教師「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的勞動者身分與事實。
顯而易見地,台灣的統治者不只明目張膽地將工人分化成所謂藍領與白領,妄圖從中游移取利,甚至堂而皇之的將受僱者區分為「工人」與「非工人」,一方面得以繼續將教師視為統治階層的禁臠與工具,另一方面,在經濟情勢日加嚴峻的當頭,又可伺機將教師打成保守反動的既得利益者,企圖藉此轉移一般受薪階級對政府無力處理經濟議題的憤怨。
由此看來,半個多世紀的天地君親師糖衣,包藏著其實正是將教師自外於整個勞動者階級,甚至是將教師塑造成階級敵人的毒藥,偏偏中毒已深的教師族群,多數仍然未能從台灣民主洪流中覺醒,原來自身徹頭徹尾就是個勞動者階級。如果自詡為專業教育工作者的教師,不能堅定地承認自身作為一個勞動者階級的事實,不能從執政當局編織的迷夢中解放出來,又該如何實現去工具化的理想呢?
其次,免不了有人極不客氣地詰問教師工會的合法性。這樣看似理直氣壯地責難,其實正意味著,統治階級對於向來作為穩定政權工具的老師,竟也挑戰起公權力的正當性是如何地不安與恐懼。
於是,政府部門和他們的應聲蟲,不僅對受僱者組織工會的基本人權視而不見,竟然還拙劣地搬出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頒布的「工會法」,意圖在教師工會成立後進行最後的困獸之鬥。
問題是現行「工會法」第四條:「各級政府行政及教育事業、軍火工業之員工,不得組織工會」之規定不僅違憲,甚至早已脫離現實如同具文,因為目前政府所屬的電信局、郵政局、鐵路局員工均已組織工會,甚至連生產經國號戰機的漢翔公司(典型的軍火工業)員工也組織工會,不僅政府未曾反對,這些公部門與軍火事業員工組織工會後,亦未曾聽聞對台灣社會帶來什麼傷害。質疑教師工會合法地位的人或許首應問問主管機關,這些被「工會法」第四條限制的工會是如何成立的?又或者這些堅持所謂「依法行政」者,主張的其實是選擇性地依法行政?
話說回來,人民行使憲法保障的結社自由根本無需政府的承認,考諸國際勞工運動與台灣工會成立之實務,大凡有實力與國家機器進行長期鬥爭者,幾乎都走在法律的授權之前,有的甚至不屑於政府的承認。眼下該關注的似乎不是追著教師工會的適法性問題窮追猛打,而是國家如何正視法律遠遠落後於現實的尷尬,如何解決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卻不承認教師工會的荒謬。
此外,也有不少人質疑,不是已經有教師會了,有必要再成立教師工會嗎?殊不知,現行教師會雖兼具有產業工會及專業人員公會之外部特徵,但實際運作起來卻無工會與公會的實質內涵。
事實上,對於法律定位不明確功能不完整的教師會,政府部門根本就沒有與之協商的認知與作為,甚至於粗暴狂妄到否定教師會的代表性,拒絕或抵制依據「教師法」與教師會協議教師聘約,在雇主與各利益團體的合作進逼之下,先天不良的教師會有朝一日恐將淪為聯誼會。
從民國七十六年解嚴以來,台灣雖然已經走過風狂雨驟的社會運動陣痛期,但從教師工會的重重險阻來看,我們離真正的公民社會恐怕還有漫漫長路要走,然而,如果教師工會衝撞體制的過程,能夠喚醒台灣社會的心靈戒嚴,讓所有的教師自覺地檢視我們在台灣社會所應扮演的角色,那以上這些反對教師工會的理由或許也無關緊要了。
(原文刊載於政策論壇電子報 第九十一號 92/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