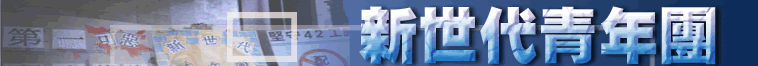本文刊登於:「新世代青年團」(http://youth.ngo.org.tw/)2004.10.11
評孫善豪《第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作品選讀》之一
何青
※編按:此文根據何青在台灣《資本論》研究會之講座錄音帶整理,由台灣《資本論》研究會秘書長丁穩勝整理。
孫善豪重譯的問題
本文要評論的是孫善豪《第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作品選讀》一書,該書包括孫善豪對馬克思著作所進行的導讀、選讀以及翻譯。我們根據的是台灣的誠品書店出版的「人文系列隨身讀系列叢書之一」,2002年5月修訂二版(初版於1999年3月)。本書內容包括:一、導讀:孫善豪〈馬克思──第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二、選讀:此部分由孫善豪重譯馬克思原著,包括有:《資本論》第一章、〈哥達綱領批判〉與〈費爾巴哈題綱〉。這三篇與其說是孫善豪的選讀,還不如說是選譯或者由孫善豪任意摘抄刪減的習作,因為每篇內容皆依他的意思而作了一些省略。本書中的導讀無疑是孫善豪對此書的序言,其內容即對上述三篇馬克思作品的導讀。另外附錄《共產黨宣言》一文,則是節選自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譯本。
首先我們從本書的「導讀、重譯」這一文體談起。我覺得一本新的翻譯書,尤其是重譯,在某種程度上必須意味著重新解釋,所以,孫善豪對這幾篇的翻譯,可以說是他本人對這幾篇馬克思原著文章的解釋和看法。他所翻譯的《資本論》第一章,事實上是重譯;另一方面,從譯文中可明顯地看出他是根據中共中央編譯局《資本論》的譯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稱《馬恩全集》))第一章為基礎,對照德文版做了他自己所認為的「必要修改」。但是在書中,他卻對抄用中共的譯本來源出處毫無說明交代,似乎中共中央編譯局的《資本論》和其他的譯本不曾存在過似的!這種拾人牙慧卻又對資料來源隻字不提的態度,即使從最基本的學術標準來看,都可發現作者的不誠實。
重譯一部重要著作的動機雖然不一而足,但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新譯本要比以往的翻譯有很不一樣的,甚至要有更進一步的成果或詮釋。《資本論》在中國的翻譯界曾經有幾種版本,而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是:中共中央編譯局參考王亞南和郭大力的翻譯的譯本;另一個譯本是法文版的中文譯本,馬克思曾對法文版的譯文做了不僅只是文字上的修改,更對第一卷的結構、內容作了大幅修改、增減;對篇、章的安排也作了修改與補充,如統計資料與說明性的註譯。同時,為了通俗起見,部分名詞也修改了。1982年中國把法文版翻譯成中文,此舉是必要的,因為法文版有新的內容,重新翻譯有助於重新研究《資本論》。馬克思在致讀者說明時特別強調,法文版在原德文版之外「有獨立的科學價值」,因為法文版可說是馬克思在完成《資本論》第二版後,又進一步修改《資本論》的重要版本。
德文版在馬克思生前才出到第二版,馬克思去世後,恩格斯根據法文版結構的安排加以修訂而編輯成了第三版。現在則是第四版(德文版全集的第四版),此即《資本論》中文版以及世界各國譯本所依據的原版本。另外,英文版由Samuel Moore以及Edward Aveling1 馬克思的女婿。根據德文版第三版所作的翻譯,由恩格斯修訂。到了1976年又有一個新的英文翻譯本 Marx,Karl, Capital, translated by Ben Fowkes ﹠David Fernbach, London:Penguin, 1976。,2翻譯者Ben Fowkes以及David Fernbach根據德文版第四版所作的翻譯。這個新譯本,除了版本更新之外,重新翻譯的理由還有:(1)多年來英語已有了新的改變,如新字彙的產生,有些名詞通俗化而有重新擬定的必要,像labor與worker這兩個字,在馬克思生前確有其意義上的區別,worker通常指的是一般勞動者,貢獻其勞動力,但並非資本主義特定生產關係中的工人;而labourer則是指僱佣勞動,在實際上指按一定時間出賣勞動力的勞動者、工人 馬克思:《資本論》(北京: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1975年),頁60,注(16),恩格斯於第四版之注。 。3然而這種區分在1970年代之後,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普遍化了,使得上述兩個字已無區分的必要,而且worker在前後文還比較接近原來labourer的含意了。(2)另外新譯者Fowkes指出恩格斯當初在審校英譯本時,為了便於讀者了解起見,把一些句子省略、刪除,現今已不需要如此處理,因此欲重現這些曾被略去的句子 。4 Marx, Karl, ibid., PP.87~88, 1976.我個人覺得,與舊的英文譯本相比較,新的英文譯本在許多地方較為容易了解、較為平易近人。談到中譯本,我們並不反對《資本論》中文譯本有重譯的空間,然而中文新譯本應該有它欲達成的目的。這些目的通常有幾點:第一點、為了改正錯誤;第二、為了使新譯本的文字更通俗易懂,或使用新的語文詞彙、或更易理解的文體來潤飾原翻譯;第三、新譯者對原著有不同的了解、解釋。如果新譯者對馬克思的《資本論》有獨到的見解,覺得有重新依新譯者自己的理解來進行重譯的必要,那麼就此點來看,重譯一事是有其價值的。第四、有新的發現或研究成果,或曾經遺漏的文字、佚文被重新發掘,因此必須重新補充,如《德意志意識形態》就是不斷有佚文加以補齊,因此重新翻譯有其必要。第五、)正如英譯本的理由,認為被原有英譯本所刪除部分必須回復才能趨近原著的意義。因此,孫善豪重譯的理由若是有意彌補中譯本的缺陷,或者,孫善豪認為他的重譯另有獨到見解,並能加以說明,則不啻為一個重新翻譯的好理由。但我讀了孫善豪重譯的《資本論》第一章,我覺得他重譯的理由很難自圓其說。首先,他把許多中譯本的缺點加強而非減弱,如增加了很多極其晦澀拗口的用語與英文式文法的句子、德文式子句加子句複雜句型,增加了更多破碎的語句,而非為了使它更中文化、簡化或口語化,來讓讀者更易於理解。
另外,孫善豪的重譯版中有許多省略處,以括號「(…)」表示,如該書45、46、50、51頁等,這些都是極重要的段落,不應被省略。例如51頁所省略處,此段原本在說明「勞動生產力」與「勞動時間」的矛盾關係,但孫善豪卻省略這段重要的論述。為何如此處理?細究其因,原來是馬克思與他的觀點不同,孫善豪在後文的一些分析中誤認為勞動生產力等於勞動力,如果依馬克思對勞動生產力的用法,那孫善豪的論述就會有問題。由此可知,孫善豪的譯文只依照自己的意思隨意作刪減或更改,才會做這樣的處理方式。再如43頁,馬克思說使用價值同時又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但孫善豪把它翻譯成「〔所有各種〕使用價值也同時是許多實物承擔者--交換價值(Tauschwert)的實物承擔者」,而在注釋1中說明「交換價值」其實應該是「價值」。因此,換句話說,他認為使用價值不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而是「價值」。但這種說法是錯的。他攪亂了形式和內容、現象和本質的分別。
再進一步談翻譯的問題,孫善豪多處將馬克思的句子按照他的錯誤認識來翻譯,甚至把馬克思原來的句子照他的意思恣意篡改,這已不是孫善豪是否能夠理解德文的問題了。他可以表明不同意馬克思的論述,說明他不同意的理由,但絕不能恣意把原著翻譯成他自己所認為的錯誤意思,且與原著有違反之處。他的翻譯除了有許多抄襲中共中央的中譯版之外,他所加上的許多觀念也是錯誤的。孫善豪重譯版的缺點倒是提醒了我們《資本論》第一章的確有值得重新翻譯的必要。由於中譯本的譯者不瞭解馬克思的現代辯證法,所以他的翻譯就使得馬克思所用的方法變得很不清楚。比如說抽象法的運用。馬克思於《資本論》〈序言〉中就指出他使用抽象法,於法文版也說:「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尚未有人在經濟問題運用過,這就使前幾章讀起來相當困難。」5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序言〉(北京: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1975年),頁26。 當初馬克思的方法沒有人用過,但現今在此方面已有許多研究。《資本論》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的中譯者,由於對馬克思的方法不是很清楚,例如對「抽象」這一辭的處理就常翻譯成「撇去」、「丟掉」或「免去」此類用詞,由此可看出中譯本譯者並未將此運用看成是抽象法的應用,而是當成任意捨去的抽象意義,而失掉「抽象」還有保存,暫時性的存而不論的含意,只是翻譯字面上的意義,而未能充分理解馬克思所運用的抽象法。因此,有些地方把「抽象」翻成「完全拋棄掉」是錯誤的。所以,如果重新翻譯的譯者能改正上述缺點,那會使有些地方的意義更清楚,從此角度看,重譯是有必要的。
前面提過《資本論》的法文版,因為熟諳法文的馬克思對法文譯本第一章做了許多修改,因此不僅是重新翻譯,甚至還做了局部的改寫與章節的調整,法文版修改的中譯文收錄在中共中央《馬恩全集》第49卷之中,所以中共中央《馬恩全集》第49卷法文版之中譯文被單獨用來作為替代《資本論》第一卷是相當普遍的作法。法文版之中譯文是個重新翻譯的特例,馬克思稱它有獨立的科學價值。除此之外,盡量保留舊有的翻譯,在處理重新翻譯工作上是很重要的實踐原則。中國在翻譯工作上是很有傳統的,就拿佛經的翻譯來說,中國曾翻譯了無數的佛經,尤以魏晉南北朝時翻譯的數量最多,他們翻譯所遵守的一項基本原則就是:前人曾翻譯過的經文、所用過的名詞,儘量繼承使用,甚至直譯。比如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大覺大悟之意,之前也有人翻譯成「大覺大悟」,但因為之後許多人採直譯,雖然許多人不知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何意,但翻譯者仍繼續沿用,有約定俗成之意。這一作法的好處,乃在於避免同一梵文有好幾種譯法而造成混亂,減低對佛經廣宣流佈的阻礙。因此中國翻譯佛經的經驗,其中有許多值得我們參考與學習之處。
而中共中央所翻譯的《資本論》,是目前中文界唯一廣布流傳的譯本,因此即使其內容有些翻譯較不好的名詞,但除非發現它譯錯或有與原著相異極大之處,否則不應該再自創一個新的名詞,例如中譯本承繼一百年來將Geld翻成貨幣,雖然通俗上Geld也有指黃金、錢幣、金幣、銀幣、紙幣等混用的情況,但通常民間所流通使用的錢與此處所稱的貨幣仍是有差距的,貨幣有許多形式、用法,而馬克思使用貨幣一詞有特殊的意義。孫善豪把Geld翻成錢,事實上不是通俗化,反而將之混淆了。6 孫善豪:〈導讀〉,《第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作品選讀》(台北:誠品,2002,修訂二版),頁15。孫文原文如下:「《資本論》終究不是寫給博學鴻儒看的,而是寫給一般大眾的。讀這第一章,唯一要有的知識背景,其實只是:『所謂商品之所以有價值,乃是因為它值錢』。」 首先,孫在第一章將貨幣翻譯成錢,乍看之下覺得「值錢」此詞似乎通俗,但是卻有令人混淆之處,到底錢是代表錢幣本身,還是貨幣的符號,諸如紙幣或是票據呢?除此之外,孫善豪文中「所謂商品之所以有價值,乃是因為它值錢」本身就是對馬克思理論的錯誤理解,一來不僅是翻譯上用一個不是很正確的字翻出(本來是貨幣卻翻譯成錢),二來因為錢的價值形式發展過程是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商品內涵的價值形式在未發展到「錢」之前,很多是以「實物」(另一個商品)作為等價物,所以並非商品有價值就是它們值錢,那也需要等歷史發展到以貨幣作為交換價值形式、交換關係發展到資本主義的階段,此句話才有意義!很顯然地,孫善豪在此方面的認識並不清楚,這種去掉歷史發展脈絡的毛病在他導讀中隨處可見,特別在孫善豪對於商品、價值的解釋。他觀念的混淆錯亂主要在於未能認清資本主義是一個發展過程,從商品切入可一步步地由「形式上的隸屬」到達「實際上的隸屬」這樣的一個發展的過程。因此,細究《資本論》第一章可知價值形式相應於不同的歷史階段而有所差異。就此點,孫善豪不但未能一究馬克思理論之堂奧,反而做了許多錯誤的翻譯。原本,由於孫善豪的重譯,除了表面上增添了許多德文文字,賣弄一下他貧乏的德語能力以外,實在是了無新意,讓吾人實在找不出他重新翻譯的必要。現在,從孫善豪倒錯的譯文看來,若要勉強找出孫善豪重新翻譯的理由,那就是他與馬克思的看法有不相同之處所耍的栽贓的技倆,這些問題我會在後面的內容一一指出,而這些是因為孫善豪本身對《資本論》錯誤的認識及誤解所致。
另外,孫善豪於該書第39頁的說明第二點,指出:「二、譯文中之引號『』係原文所有;引號「」則為譯者為閱讀方便所加。」由此可知譯文依孫的意思加了許多「」,而由文中可見許多「」並不是馬克思原意,孫認為「」為閱讀方便所加,我卻認為閱讀起來一點兒也不方便,反而有與馬克思原意及所加重的部分有混淆之處。而孫書的第四點認為:「四、《資本論》第一章之注釋,許多皆涉及經濟理論史之爭論與問題,對於讀者恐怕無直接關係,故原則上均予刪除。」我認為他這樣的處理方式,真正目的恐怕不是如此,恐怕是因為翻譯這些注解是很麻煩的事,因為必須要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著作、學說、學者有相當的瞭解,才能進行翻譯。平心而論,中共中央中譯本將這些注解翻譯的還不錯,而這些注解正好是《資本論》副標題-─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要設置的對立面,即威廉配第以降,從亞當斯密一路到李嘉圖而集之大成的古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常常以注解的方式來表示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因此注解一定要閱讀,否則就無法瞭解馬克思所要批判的對象、理論及其錯誤為何。而且這些看法在《資本論》第四卷《剩餘價值理論》中有更多的敘述,其內容為馬克思對於在他之前關於剩餘價值理論的所有的重要著作、作者、思想與方法,作了相當深刻且犀利的總批判。孫善豪將注釋免除,並將之窄化為只是經濟理論史爭論的問題,顯然是不了解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資本論》不可分割的要素。事實上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及庸俗的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對今日的主流經濟學仍然適用。目前主流經濟學的看法仍繼承以很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錯誤觀念,所以馬克思的批判對於瞭解目前許多思想、爭論是有助益的。
除了一些注解被省略掉了外,從孫善豪的翻譯,可以發現他對辯証法簡直是一竅不通,因為他連一般辯証法的觀念也不很清楚,尤其從他對〈哥達綱領批判〉、〈費爾巴哈題綱〉兩篇著作翻譯的甚多處錯誤可以得知,而且有很多基本觀點他也搞不清楚。此種混亂與他對《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許多概念不甚清楚是相同的。比方說「勞動」與「勞動力」;以「勞動時間」作為「價值衡量的尺度」跟「勞動」作為「價值的尺度」,或者是說用勞動作為社會生產與分配的原則,有很大的不同的意義,這點他是搞不清楚的。另外他對歷史的發展、歷史與邏輯相互的關聯也不甚明白。他對於抽象與具體間的關聯、形式與內容、表象與實質這種對立統一的關係也認識不清。他的觀念中不存在對立統一的概念,只有很粗淺的形式邏輯矛盾觀。現在我們就從他的導讀來証明上述的批評。
對孫善豪導讀之批判
導讀的題目是「第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此也是這本書的標題。這句話本來是馬克思對他女婿所說的,因為當時許多曾被馬克思批判過的人如普魯東派、拉薩爾派之流趨於時尚突然都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在此種情形下馬克思遂自嘲說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孫善豪的導讀給人的第一個誤導印象是他在替馬克思辯解,並且捍衛馬克思,而非反對馬克思。台灣早期反對馬克思的工作是由一群反共專家負責,但他們的批判往往是很膚淺的,在台灣進入國際分工體系後,隨著留學生人數大大增加並且與中國往來日益密切,很少人會再相信那些反共家族的話,今天那一套反共反馬的八股說詞可以說完全沒有說服力了。因此,孫善豪在該書12頁所表達的憂慮「透過國家教育等所謂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往往就被篩選和沉澱成一種對馬克思的刻板印象…。」早已不是問題所在,像孫善豪這種故作姿態的杞人憂天,無非是想霸佔馬克思理論的詮釋權而已。因此,值得令人更深層地憂慮的,反而是孫善豪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對馬克思理論的誤導,因為一般人早已不能接受簡單的曲解。因此以導讀形態出現的幾本書,包括我以前批判過的高安邦7 何青:〈評高安邦的「《資本論》導讀」〉,參見新世代青年團網站(http://youth.ngo.org.tw/theory-movement/theory-capital-000.htm)。高安邦的導讀只見於台灣時報出版社版本的《資本論》。 與孫善豪的導讀莫不使人感嘆台灣初學者在讀《資本論》的道路上攔路虎之多!孫善豪與高安邦的不同在於,高安邦可以算是反共家族的年輕一輩,而孫善豪則屬後反共家族。他可能不是反共家族的嫡傳弟子,因此,無須對以前反共家族對馬克思的曲解負責任,他是在此背景下重新導讀馬克思的著作。他的導讀若有助於了解馬克思,那當然值得欣喜;但若是進一步誤解、扭曲馬克思,那就和先前的反共家族如鄭學稼、胡秋原、高安邦、李英明等人就沒什麼兩樣了。事實上,孫善豪所呈現的與他們不同,他以一種比較同情的眼光來看馬克思的東西,換句話說,他有自己的角度而不同於傳統的反共家族。因此我們可以說,他是以批判反共家族的面目出現,重新介紹一套虛假的馬克思主義。
孫善豪在導讀中提到:「誰能理直氣壯地宣稱自己讀過馬克思呢?只能是那些讀過《資本論》第一章的人。」(14頁),就此意義而言,他當然要對中文本進行「更精確的」翻譯。但就孫善豪的譯文來說,就像本文之前所提到的,實在找不出任何重譯的理由,因為他不但沒有推陳出新的看法,反而帶入了許多顛倒錯亂的見解。我想,他之所以要進行重譯的最大理由,是想將自己對《資本論》錯誤的想法植入(置入)重譯中,從他的書中可發現,就這點而言,他著實花費了不少功夫。
先說幾個枝微末節的小錯誤:一、14頁注解2中他提到的「第一節」應該是〈第一篇〉。二、他說目前通行的《資本論》是第二版。事實上,第二版與第四版有一些結構上的改變,這是恩格斯參考法文版後所做的修訂。而我們現在看到的《資本論》第一卷不論是中文版或英文版,以及全世界各種文字的翻譯,都不是德文版第二版,而是第四版。孫善豪這本書所選的第一章也是取自第四版,因此他在注2中說目前流行的是第二版是錯的,恐怕是指德文的發行而言。然而這些小錯誤,若比起他對資本論的曲解,實是微不足道。三、孫善豪在15頁又引了列寧的話「不了解黑格爾『大邏輯』,就讀不懂《資本論》,尤其是第一章」,並認為列寧在危言聳聽。注解3也說,列寧這種說法太誇張。可是,我們若看看《資本論》第二版的〈跋〉,中文版的24頁,馬克思說:「我的辯証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証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觀念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8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序言〉(北京: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1975年),頁24。「辯証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祕化了,但這決不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証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裡,辯証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祕外殼中的合理內核。」9 同上注 這個〈跋〉事實上印証了列寧的說法,亦即要了解黑格爾的「大邏輯」,才能了解第一章,這絕不是誇張。第一章事實上包含了很多馬克思對辯証法的看法,只是他的辯証法與黑格爾不同,他把黑格爾倒立的邏輯學導正過來了。我將馬克思所稱的「我的辯証法」稱為「現代辯証法」10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稱之為「現代唯物主義」,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364 。 。我也不贊成很多研究《資本論》的學者如日本學者宇野弘藏與蘇俄的盧賓(I.I. Rubin)以及許多中共官方對《資本論》的注釋與講解,他們常錯誤地把馬克思《資本論》裡的方法當做黑格爾辯証法之運用,因此把《資本論》裡所用的方法用黑格爾主義的方式來解釋,此觀點也是不正確的。這兩種說法明顯違背了馬克思自己在第二版跋中對自己方法的看法。孫善豪顯然不了解這些關係,他不明瞭列寧並不是要讀者以黑格爾的「大邏輯」解釋,列寧之意是讀了「大邏輯」,有了辯証法的基本觀點後,才比較容易了解第一章。我認為此說法在某種層次上是正確的,雖然了解第一章不應該依照黑格爾的邏輯學,而是應倒正地了解。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裡,馬克思對他於〈《資本論》序言〉中所提的抽象法作了一番敘述。馬克思曾想對這個方法做系統的整理,在給恩格斯的信裡曾提及他想用三至五張的稿紙數,將他對辯証法的了解寫下來。可惜的是馬克思過世後,恩格斯整理他的遺物,卻始終遍尋不著這個手稿。不過就如列寧所言,《資本論》為我們留下了馬克思的辯証法。
孫善豪在16頁又講到civil society,並以此字大做文章。這個字最早被顯著地使用,當屬黑格爾,後來馬克思在很多地方也都用了這個字,《資本論》裡也有出現。就當時的社會而言,馬克思用civil society此詞所指的是資產階級,描述的是資產階級社會。這從《資本論》的上下文可以清楚地發現。雖然孫善豪認為這是第一點要說清楚的,但我認為他將其重譯為「市民」,反而使讀者頭昏腦脹、混淆不清。
關於erscheinen和darstellen的用法
其次,孫善豪又提到兩個字,而這也可以說是他最得意的兩個字即德文的兩個動詞:erscheinen和darstellen。erscheinen是通常所指的「表現」,darstellen則是語句的表達,即這個語句表示什麼。孫善豪把這兩個字混同起來,並認為這兩個字事實上時常有相同之意。但,這兩個動詞的含義可說千差萬別,一點也不相同。
孫善豪在16頁提到:「這兩個動詞的重要,只要看它們不斷連接著商品、價值、價值形式等等核心概念,也就可見一般了。」我們可以發現,他僅僅把這些東西看成是概念,對他來說,商品並不是一堆一堆很具體的物、客觀存在的物,有各種各樣看得到的、感覺得到的,可以滿足人們需要的使用價值,而只是一個存在於腦中的概念,這些概念在這裡被動詞表現出來,這與我們在前面所提馬克思的方法,完全是大相逕庭。
孫善豪接著又提到:「尤其,如果《資本論》的第一句話可以算作是《資本論》最重要的一句話,那麼它的動詞正好是erscheinen,就更不可等閒視之了。」(16頁)他看到的第一句話和我看到的第一句話似乎不太一樣。他的第一句話是指商品的積累,而我看到的卻是資本主義佔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erscheinen是要表現一個東西,例如價值形式是要表現價值。darstellen則是一個語句,舉例而言,二十碼麻布等於一件上衣作為一個語句和作為一個等價形式有何不同?作為一個語句,它是一個對等的關係,這兩個詞可能有量上的差異,但它們處於對等,此種相等不是一種數學上的相等。但當我們講到價值形式時,「二十碼麻布等於一件上衣」,所「表達」的則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係,等號的左邊與右邊是互相依賴卻又互相排斥的。以這個例子來說,一件上衣是作為等價形式出現,二十碼麻布則是作為相對價值形式出現。這兩個物在價值等式裡是互相依賴,但它們也互相排斥。於此我們不能說A等於B所以B就等於A。當上衣扮演等價形式時,它就不能再扮演相對價值形式的角色。《資本論》第一卷的62頁裡描述的很清楚:「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是同一價值表現的互相依賴、互相條件、不可分離的兩個要素(moments),同時又是同一價值表現的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兩端即兩極」11 馬克思:《資本論》(北京: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1975年),頁62。 這就是在描述對立統一的關係。二十碼麻布等於一件上衣,從語句裡我們看不出它們的矛盾,但由價值形式中我們可發現,這兩者事實上隱含著矛盾的關係,而且互相排斥。因此,簡單地由語句、語法、文法、寫法來讀《資本論》,相較於把它看成一種價值形式,並以馬克思的抽象法來了解它們彼此間的關係,會有很不同的意義。在語句裡是不容許互相矛盾的,我們不能說二十碼麻布等於一件上衣又不等於一件上衣,因為這違反了文法上的不矛盾律。但在解析價值形式時,若一件上衣是二十碼麻布的等價形式,它就不能再變成相對價值形式,若你堅持將上衣變成相對價值形式,那它就不再是等價形式。另外,它也不能使自己與自己等同,二十碼麻布等於二十碼麻布在語句裡是成立的,雖然這是一種同義反覆,但就價值形式而言,這個等式就完全沒有意義。因此,我們講的是價值形式中的等式,而非語句裡的等式。
有了上述的認知,我們再回頭看看孫善豪的講法。孫善豪很簡單的把erscheinen和darstellen看成是動詞,它們都是表現商品、價值、價值形式。他在強調erscheinen這個動詞的重要性之後,又說到:「而如果『勞動的雙重性』是馬克思所『首先批判地證明的』、並且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解』所環繞的起跳點,那麼,這種雙重性並不是就勞動本身可見,是『表現在商品裡的』──這裡的『表現』(dar-ge-stellt)也顯然應該具有某種關鍵性地位了。」(p.17)
孫善豪在這裡只是強調darstellen是語法的用法。事實上,馬克思提到所謂「首先批判地證明的」,批判的對立面即是古典政治經濟學,而這些批判往往表示在他的注解裡。孫善豪將《資本論》第一章裡的許多注解省略掉,恰恰使馬克思不能「批判地證明」他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相異處。《資本論》第一章裡的每一句話,幾乎都有其針對批判的對象,皆是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這似乎是孫善豪所不了解的。
另外,馬克思所說的「起跳點」主要是講「勞動的二重性」。透過捨象法,我們把一個商品的使用價值捨象後,看出它是一個勞動的產品。從勞動產品的具體性,看出它們具有各種不同的具體勞動,這些不同的具體勞動要能產生交換,一定要使它們能夠共同,要有同質和可公約的單位。因此,整個地一般化、平均化、抽象化以取得抽象勞動這個觀念,就成為實際上的一個存在。馬克思將它解析出來後,認為它就是價值的實體。透過對價值形式的分析,馬克思讓我們了解到從簡單的、偶然的價值形式演變成交換價值形式是一個發展的結果。在商品交換日益頻繁的情況下,需要尋找一種既可以進行物化勞動同時又合乎交換需求的等價物,而它可以作為價值的尺度,此物就是貨幣形式。從不完善的簡單價值形式,慢慢發展到最完善的貨幣形式,是一個不以主觀願望為轉移的過程,而是客觀社會發展的結果。如果以馬克思的言語來描述,則是「在發展的過程中,貨幣就被排斥出來了 。」在馬克思的分析裡,「勞動的二重性」這兩重完全是互相排斥的,即使用價值這一重與價值這一重是互相排斥的。價值這一重裡,不存有任何一點物質屬性,而是一種社會屬性、社會關係。從使用價值裡,我們也找不到任何一個價值的原子,只能觀察它的物理、幾何、化學的屬性,而並不包含有任何的社會屬性。因此,一重是物的自然屬性,另一重則是社會的屬性,此即馬克思所說的二重性,它們是互相依賴卻又互相排斥的。
我們這邊來看看孫善豪是怎麼了解的。在17頁他寫到:「某乙在某甲中被dargestellt出來,那麼某乙是「包含」在某甲裡的。例如:勞動是在商品裡被表現(dargestellt)出來的,則商品包含著勞動。」
孫善豪這種講法是非常簡便的,我們可以發現商品、勞動對他來說只是幾個語句上的相互關連,在20頁的最後一段表現的更明顯。這裡的「價值存在(Wertsein)」這個字在中共中央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的67頁也有提到。在這裡,馬克思主要是說德文的Wertsein這個字不夠精確,不能表達價值的意義,並認為日耳曼語的valere好多了 。12 前揭書,頁66~67。沒想到孫善豪在這裡竟然拿這個字玩起「造句」遊戲:「二十碼麻布ist(sein的第三人稱變化)一件上衣wert。因此,一個商品的『價值存在』,其實都可以變成一個表達、一個句子。或者反過來說:只有造出一個句子之後,一個商品的『價值存在』才被表達出來。而這個句子,也就是這個商品的『價值形式』或『價值表達』。」
他把價值形式、價值存在與價值表達完全看成是語句的關係。再回到17頁,他講的也都是一種語句的關係,他完全混淆了erscheinen和darstellen這二個字的意義。因此,貨幣形式表現了價值或一件上衣表現了二十碼麻布的價值,對他來說只是一種語句、造句子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馬克思是在說明價值形式而不是在說這種句子之間的關係。研究價值形式的來龍去脈與研究「二十碼麻布等於一件上衣」這種語句,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孫善豪的「別名法」和「配對法」
由於孫善豪純粹是從語句的關係在看問題,他就沒有辦法發現背後「對立、統一」的關係。這一點也反映在他在17頁接下來提出的第三點:「四個最核心的概念:有用勞動、抽象人類勞動、使用價值、價值。它們各有很多『別名』,在這裡也許不妨列出來:「1.有用勞動=具體勞動=特定的、依目的而進行的勞動=實際勞動;2.抽象人類勞動=相同人類勞動=無差別的人類勞動=人類勞動=勞動力;3.使用價值=有用性=商品體=物品=使用對象=勞動產物=財富;4.價值=價值物=價值對象性=價值存在=價值體=價值實體=價值量」
我們看到,他是用「別名」的方式把不同的概念等同起來。他上面所講1到4的等式,是把由抽象法得到的現象與本質、形式與內容間的辯証、對立統一關係都免掉了,而把它們看成是單純名詞的等同問題。如第一個等式:有用勞動=具體勞動。這二者並不相等,馬克思就是從有用勞動出發,將有用勞動中包含的具體勞動捨象掉,才得出抽象勞動的概念。所以,有用勞動也包含著抽象勞動。現在孫善豪將有用勞動與具體勞動等同起來,那我們如何得出抽象勞動這個範疇呢?在他的概念遊戲裡就是要把這些名詞等同起來,好像馬克思只是把這些名詞用別名表示出來。孫善豪的方法可以說是「別名法」,迥異於馬克思的抽象法。
第二個等式亦然,以勞動力為例,勞動力和其它的商品一樣,而它的有用性就表現在具體勞動上且是特殊的具體勞動,勞動力的特殊職能使得抽象勞動與具體勞體可以並存,這也使它有別於一般商品。勞動力儘管有其特殊性,但它作為商品與其他商品相同,都有質、量,都需要再生產,都是勞動產品。因此,勞動力並不等於抽象人類勞動,它在進行抽象人類勞動時也在進行具體人類勞動;它在進行個別勞動時,也在進行社會勞動,它是一個特殊的商品,它的職能就是勞動。孫善豪用名詞把它們等同起來,就完全看不出這些意思,甚至會扭曲這些含意。
馬克思曾指出,使用價值不一定是勞動產品,也可以是自然物,比方說:空氣、水等等。因此第三點,使用價值並不一定等於勞動產物。孫善豪在這裡的「等」,實在看不出什麼意思,既不像數學的等式,也不像「等價」。他在這裡就是「別名」,是由他的別名法出發。如果別名法真的有助於理解事實,我們就不需要科學了。
再看第四點,事實上價值量只是衡量價值的一種方式。古典政治經濟學一直到李嘉圖,都太重視「量」,只是從量上去考量價值。但馬克思已經說過,從量的關係是不能抽象出價值的。從兩個不同使用價值的交換關係,我們無法抽出勞動時間,要得出勞動時間,我們只能脫出使用價值這個範疇,由「勞動產品」這個範疇用捨象法一步一步的得出來。古典政治經濟學由於沒有這個方法,便無法得到馬克思認為的政治經濟學的樞鈕: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這是社會的實體,它是從勞動形式入手去找勞動的內容、它是實質。這裡面隱含了馬克思的方法,孫善豪不了解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不只是一個語句的關係,他說:交換價值是價值的價值形式,這除了把兩個名詞連接在一起,並不能界定什麼東西。
在這四個等式之後,孫善豪在第19頁又將這種「別名法」予以精練。他寫到:「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個方面,對應著勞動的兩個方面。因此,這四者之間的關係,是兩兩成對的:1.『商品』和『勞動』之間就有一個對應關係:商品由勞動生產出來、勞動則表現(darstellt)在商品裡。2.『有用勞動』產生『使用價值』、『抽象人類勞動』形成『價值』。3.『有用勞動』是『抽象人類勞動』的表現形式(或實化形式);『使用價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或實物承擔者)。4.『有用勞動』與『價值』之間、『抽象人類勞動』與『使用價值』之間,則沒有任何直接關係。它們要發生關係,只能透過中介。」
繼別名法後,孫善豪又使用了配對法,企圖用演繹、排列組合的方式將這些名詞兩兩成對的排列起來,這樣就產生許多相對應的關係。而這些關係的中介物,就是依靠他所說的「表現」這個字。因為他把「表現」與語句的「表達」混為一談,造成他以為用「表現」就可以把所有的名詞連接起來,分雙配對。我們來看看他是怎麼配對的。第一點,他說:「商品」和「勞動」之間就有一個對應關係。問題是,商品、勞動在孫善豪看來只是二個概念,從這二個概念怎麼能看出什麼對應關係呢?孫善豪對此並沒有做出任何解釋。孫善豪顯然認為只要找一個動詞將二者連結起來就可以了,而他找到的動詞就是表現(darstellt) 。13 這個字事實上應譯作「表達」。事實上,商品價值形式的內含是勞動(抽象勞動),是慢慢發展出來的,它起初只是一種偶然的現象,一直到貨幣形式才達到最完整的情況。第二點我們先略過,直接看第三點。孫在第43頁也提到與這點相關的話:「使用價值也同時是許多『實物承擔者』──交換價值(這裡的交換價值其實應該是價值)的實物承擔者。」
事實上,馬克思講這一句話時,價值的範疇還沒有出現。從使用價值與使用價值的交換中,我們只能看到交換價值這個形式,我們或許可能查覺到有第三者的存在,但並無法得知這個第三者就是「價值」。換句話說,我們無法得知使用價值就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因此,孫善豪認為這裡的交換價值要改成價值,完全是搞混了,實在是沒有進入狀況。
像孫善豪這樣單純將兩個名詞連繫起來,只是從概念到概念,完全看不出演變的過程。馬克思在〈評阿瓦格納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曾再三強調,他的研究法不是從概念到概念,遺憾的是,孫善豪卻還停留在馬克思所批判的層次。再回到第三點,使用價值要成為價值的實物承擔者,要發展到一定的價值形式下才可能,而不是將兩者連起來,並插入一個「表現」就可以。第四點就更可笑了,有用勞動與價值間是有一定關係的,若沒有有用勞動就不可能形成價值,孫善豪卻說要透過中介,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找不到名詞來「表現」了,只好通過「抽象人類勞動」來中介,這樣一來,這二個名詞就又發生關係了。他在20頁又說到:「這樣的兩兩相對的關係,是商品內部的對立關係。」但是為什麼兩兩相對的關係,就是對立關係?這兩者並無必然性。事物的變化是有對立關係,但並不是說將兩個概念湊在一起就會變成對立關係。孫善豪又說:「但是如果只看一個商品,那麼即使把它翻來轉去,也是看不出這種隱藏在它內部的關係的。因此,要把它指認出來,就要看它的『表現形式』,也就是價值形式,價值關係或交換價值。」(20頁)
我們看到,「表現形式」似乎變成了一個很好用的工具,孫善豪看不到的「內容」他就把它歸為「隱藏在表現形式的內部關係」就解決了,但這並不是分析,更不是馬克思的分析。
孫善豪書中又說:「馬克思提出了四種價值形式:簡單價值……、錢的形式 。14 應該是「貨幣形式」。這個部分是馬克思主要在『賣弄黑格爾表達方式』的地方。」(20頁)
事實上,這裡一點也沒有賣弄什麼黑格爾的表達方式,而是馬克思所獨創的辯証法。唯有透過這四種形式,才使我們識破價值形式的神祕性,並能進一步了解貨幣形式的奧妙。這裡絕對不是什麼表現形式的問題,更不是孫善豪所想像的,以為任何問題都只是表現者與被表現者間的混淆。馬克思對這四個形式的分析,一點也不是黑格爾的表達方式。因為黑格爾的方法是由抽象出發,慢慢地愈來愈具體,然後就變成現實,理念可以具體化並產生國家、君王、家庭、所有權等一切。相反地,馬克思的價值形式是二個完全不同的形式互相依賴,卻又互相排斥,它是一個對立統一的關係,一點也不是黑格爾的表達方式。孫善豪完全不能領略,而把它們都看成一種語句的關係,因此他在21頁又寫到:「只有造出一個句子之後,一個商品的『價值存在』才被表達出來。而這個句子,也就是這個商品的『價值形式』或『價值表達』。」
他把馬克思對價值的分析簡化到只要造一個句子就解決了。他不了解價值形式背後不只是概念的問題,而是隱含了現實的社會形式,馬克思講的是交換關係、生產關係、資本、利潤、利息、工資、地租等等具體的東西。用別名法和配對法來扭曲馬克思的現代辯證法,這是頑皮的小孩在牆上塗鴉罵人的手法。孫善豪的做法對他自己也是很不公平的,如果有人試著把孫善豪教授、台灣社會研究、左翼、假左派四個詞用別名法和配對法來造一些醜化孫善豪的語句,請問:他不是只有啼笑皆非了嗎?
(待續)
※注釋
1.馬克思的女婿。
2.Marx,Karl, Capital, translated by Ben Fowkes ﹠David Fernbach, London:Penguin, 1976。
3.馬克思:《資本論》(北京: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1975年),頁60,注(16),恩格斯於第四版之注。
4.Marx, Karl, ibid., PP.87~88, 1976.
5.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序言〉(北京: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1975年),頁26。
6.孫善豪:〈導讀〉,《第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作品選讀》(台北:誠品,2002,修訂二版),頁15。孫文原文如下:「《資本論》終究不是寫給博學鴻儒看的,而是寫給一般大眾的。讀這第一章,唯一要有的知識背景,其實只是:『所謂商品之所以有價值,乃是因為它值錢』。」
7.何青:〈評高安邦的「《資本論》導讀」〉,參見新世代青年團網站(http://youth.ngo.org.tw/theory-movement/theory-capital-hsu.htm)。高安邦的導讀只見於台灣時報出版社版本的《資本論》。
8.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法文版序言〉(北京: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1975年),頁24。
9.同上注。
10.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稱之為「現代唯物主義」,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364 。
11.馬克思:《資本論》(北京: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1975年),頁62。
12.前揭書,頁66~67。
13.這個字事實上應譯作「表達」。
14.應該是「貨幣形式」。